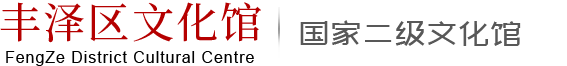作者:唐涛甫
一
母亲撒手人寰离我而去已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日日夜夜,不可胜数的风霜,多少浮沉的世事,尽从我脑海中烟消云散,甚而至于已忘却。唯独母亲眼眶里悬挂的泪珠,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父辈因海外关系的缘由,我的童年在周围人群的白眼下度过。那时我贪婪地望着“红孩子”腰间背着的腰鼓,期盼能与这群小学生一样也在自己的腰间背上它。难忘的一次,一位同学叫我帮她扶着腰鼓,让她把系着腰鼓的红绳子在腰间绑紧,当时我以为她已绑好它,就松了手,万想不到她自己绑不紧,瞬间,腰鼓掉在地上,红漆脱掉许多,她哭了,跑到校长面前告状.校长板着脸走过来,不分青红皂白,气冲冲地朝我训骂一顿,最后,强硬地叫我把腰鼓带回家,逼迫我一定要买个新的赔学校。我呆住了,深感无端的冤枉又无可奈何,在极端的痛苦和害怕中,我泣不成声,斯时,家中穷得连三餐的锅盖都很难揭开,哪来的钱去赔?
我硬着头皮,带着损伤的腰鼓到家中,在母亲面前大哭一场,母亲深知我蒙受冤枉,无奈于“特殊气候”所酿造的悲剧,她看到我哭得那么伤心,她反而不哭,劝我:“别哭了,叫父亲想办法到泉州向朋友借钱买个腰鼓赔吧!”
父亲冒着风雨立即从乡下到泉州为我去办这冤枉事。我瞧着母亲红透了的眼眶,泪珠却没掉下来,只见到她的双手在颤抖。是怕、是气、是与我一样受委屈……斯时我无暇理解母亲的心理活动。
父亲从菲律宾回国后,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他被扣上“帽子”,家境的竭蹶潦倒,又为我负债赔了腰鼓,童年的我只好与双胞胎的弟弟告辞学校,迈出学校的门槛。这时我第一次目睹母亲眼眶里的泪珠真的滚下来。
二
双胞胎的弟弟被我株连,年幼的我俩只好一起辍学,种田力不从心,买头小牛又没本钱,一字不识的母亲,也无奈地把久挂在墙上父母结婚时的一对镜框(是海外书法家为其挥毫的“合欢被里鸳鸯睡,连李枝头蝴蝶飞”)解下来,拿到泉州市当铺当卖,这对精通古文和书法的父亲来说是舍不得与他相伴几十年的家宝割爱的,束手无策中的父亲只好把它卖了两块钱,好让我与弟弟进泉州市购买些熟花生、蚕豆、饼干、糖果之类。第三天,弟兄俩抬着一个箩筐,上面搁着簸箕,排放些小食品,在小学门口做起小本生意,怀着无端失落感的我,饱尝进出校门师生的白眼与奚落。每当学校上课铃声一响,从学校里传出铿锵的铃声及琅琅的读书声,似乎重重地撞击我那幼小的心灵,撕裂我那颗沸腾柔弱的心。
课后,围着我小箩筐的,总是那刚进校门、还在受启蒙教育的同学,尽管寥寥无几,他们也让我感到一点点的生意和丝缕的温馨,我不敢直面正视从身边走过的老师和同班同学,他们似乎在冷落我。
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故意把我的箩筐踢倒,花生、蚕豆、糖果之类的小食品撒落满地,我与弟弟一粒粒地把它们捡起来,抬着箩筐哭着回家,母亲看到儿子的可怜相,真的大哭一场,随之找这位同学家长论理。
冬去春来,细雨飘飞,春寒料峭,我与弟弟穿着单衣、单裤,打着赤脚,从农村家中步行十多华里到泉州市补充小食品,往返近三个小时,一进家门,母亲发现我与弟弟冻得浑身发抖,小嘴唇发紫,她的眼眶红了.泪珠悬挂在脸上,急忙帮我俩换衣服,烧红“火窗”(竹篾做的小木炭炉,用于烤火取暖)中的木炭,让我兄弟俩上床,双脚躲进棉被里,随之端来碗热姜汤,再放些红糖,母亲发现我一直瞧着她润湿的双眼,她终于说了一句:“孩子,父母太没本事,让你俩兄弟那么小就受苦!”
三
我深知,母亲曾是位小麦韭菜不分的城市小姐,外祖父母认为能攀上泉州城内外典型的侨家,已是再美不过了,谁料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父亲回国后,再无法南渡海外谋生。特殊的年代,父亲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家庭生活日趋贫寒,为了与家中窘迫的生活抗争,母亲只好给人租地,扛着锄头,肩挑盛着肥料的木桶,打着赤脚,踩在山间崎岖的小道上,从城市的闺秀,到农村的单干户、便工队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步步走进淳朴农民的行列。经风雨、冒寒暑,她无怨无悔,很难看到她掉下一颗泪珠。而每当我看到母亲打着赤脚,脚背那道道的裂痕,血丝沿着裂痕渗出来,我不禁为之感到心酸而掉泪。
四
20世纪 50年代初的寒冬腊月,父亲每晚得进政治学习班改造自己,总得在子夜才回家,母亲总守在“鸡母灶”边为父亲煮咸地瓜汤,放些芥菜,好让父亲回家后抵御寒气。每天夜晚,我总偎依在母亲的身旁陪伴她。“鸡母灶”里通红的火光照着母亲瘦黄的脸,照着她对生活充满的顽强信念,照着她对儿子的期盼。
1952年,我转学到邻村三省小学,虽已是春天,仍是寒风伴着绵绵的细雨。我打着赤脚,身体哆嗦着,傍晚放学,我到粮店买了二十斤大米,分装在两个草袋里,用竹扁担挑着它,小心翼翼地沿着泥泞田间小道行走,脚板冻得麻木,一不小心,人滑倒,大米撒落在泥泞的土里,我急得哭起来,把混着泥土的大米捧到草袋里,我深知回家一定要受到母亲怒骂,甚而准备挨打。回到家中,我急得大哭,母亲看到我的脚板已发紫,还有哆嗦的身体,她不骂一句,父亲有点发火,母亲反而劝着父亲:“孩子小,没力气,下雨路又滑,别怪他。”说完,她打了温水让我洗澡。随后,把二十斤大米分别倒在盛满水的木桶里,把米洗净,向邻居借来几个大簸箕把它晾起来……
五
1954年,我幸运地考上泉州市晦鸣中学,母亲囊中羞涩,为了给我凑合一元六角钱的报名费,只好把家中唯有的五斤大米背着我卖了。一家六口,明早就断炊了,母亲只好将菲律宾带回来的一个楠木梳妆台桌给邻居,换来五十斤谷子。我总认定母亲是含泪割爱它,相反,她没哭,反把谷碾成米,让我捎带两斤到泉州姨妈家中寄午膳。
1957年盛夏,投考高中,学校只录取百分之十,倘若我落取,身矮体弱,肩不能重负,不能耕耘田园,连抗旱蹬“水车”都生怕掉下来,唯有选择寒窗苦读。
繁忙的夏收夏种,正逢我回家躲在阁楼上自学准备投考高中。一天晌午,艳阳当空,母亲头戴斗笠,肩扛锄头,满头大汗,一进门,看到锅中连稀饭都没有。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大发雷霆,责备我:“我那么辛苦,你连帮我烧壶开水都不肯。”此时此刻,我恍然猛醒。是啊!我太自私了,虽然生怕考不上高中,落得俗话说:“文不像书生,武不像枪兵。”我深感无限的内疚,这次我以为母亲会为此掉落泪珠,会用她的泪水取得我对她的同情,然而,恰恰相反,她洗完脸,忙于煮中午饭。母亲这次不哭,我心中比哭来得更难受,也许她的泪是往肚里吞咽的。
一个月过去了,录取与落取的同学前三天就通知了,唯有我渺渺茫茫。母亲终于在我面前开口:“绝对没希望了,你肯定要当农民了。”于是,我径直地跑了十多华里到泉州,找到原班主任,她告诉我:“你考进泉州七中。”我二话没说,告辞了班主任,掉转头,快步如飞地返回家中,把这特大的喜讯告诉母亲,她听了,为我高兴,激动得滚下泪珠,我抱着她一起哭了。
考上的同学全部报名完,唯独我报名费还在天空飘呀飘呀。
为之母亲专程到泉州市求助于姨妈,她从姨妈处借来我的报名费,带来姨妈他们中午吃剩的冷饭,带来一支接近报废的钢笔,我喜极而泣……
六
1972 年我从清流山区返回故乡,母亲给我一封信:“孩子,如果你有能力养我,我多想回到你的身旁。”是年,农历二月初二是我的生日,母亲为我特地从福州带来八个煮熟的红蛋。她一看到我就高兴得淌下眼泪,然而,她这次回泉州乡下老家,再也爬不起来了。同月初五,我与其他老师调课,向学校请假半天。我守在母亲身旁:“母亲,你今天精神好多了,是否病好些了?”她微笑地摇摇头,眼眶有些湿润,翌日,她撒手人寰,与这个无所作为的儿子永别了……
今天,我才明白母亲永别的前一天是回光返照,我仿佛透过她那无声语言中的脸孔,发现泪珠是往肚子里咽下的,此时此刻,我仿佛又听到她在农村积肥时,肩挑畚箕,告诉挖潭泥的侄儿说:“侄儿,我又来了。“她希望侄儿能在她肩上的畚箕里少放些潭泥。
是啊!于母亲年迈时不应让她再肩负生活的重担,深感无限内疚的我今天依然能看到她对生活充满热爱和任劳任怨的目光所折射出的慈母的包容,我仿佛又看到母亲眼眶里那一颗颗充满母爱的泪珠。
(文章原载于《丰泽文学》2020年·夏之卷 总第53期)